你該去看精神科了:當你這樣說的時候,想不想知道我們的世界長什麼樣子?
【更新】這篇文章是林奕含在去年 1 月時寫下的,今年 2 月她剛出版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,出版後,更多人認識了這位 26 歲的才女。她的文筆讓人驚艷,但同時那份細膩和早慧的滄桑痕跡也讓人不捨——這是用什麼樣的痛苦才能淬煉出的文字?昨日她的離世被出版新書的 游擊出版 證實了。許多人措手不及,我們沉痛地感到遺憾,但或許對她來說只是不再受世界折磨的解脫。【為什麼挑選這篇文章】該去看精神科了,常常聽見這樣的玩笑話。但真正的病院裡,是什麼樣子呢?與作者相談,覺得這篇的原意單純是想闡述,她自己在社會中作為大家口中笑話的精神病病人的感受。並不是生病就很了不起,拿來要求大家政治正確——生病這件事情帶來的感受實際上很荒蕪,記錄下來只是想傳達這樣的感受和無助。(責任編輯:林芮緹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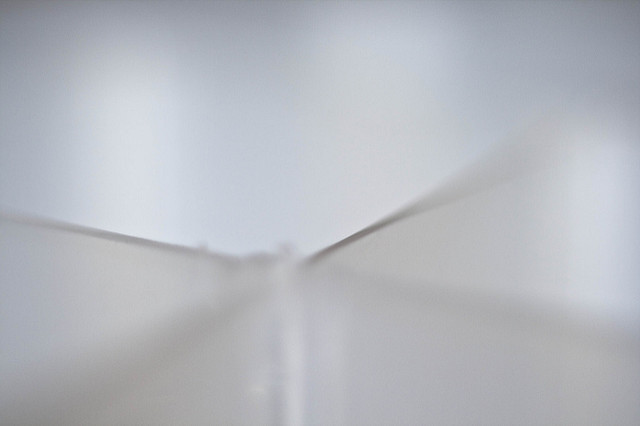
文/ 林奕含
旁觀網路筆戰,無論什麼議題:性別、省籍、薪水、麵包,筆戰至酣,一旦有人拋出卑劣的詞彙或偏激的觀點,反方一定會有人說:「樓上該去看精神科了。」或者生活中遇到暴虐的客人,怠慢的上司,人也會罵:「有病就要看醫生!」
我 常常想起精神病院的時光。拆鞋帶、沒有沸水、不能用刀叉、不能用玻璃、瓷器、不能用橡皮筋。放飯了,每個人用鐵湯匙切著排骨,那熟練讓我心痛。生命在此忘記連續性,病院的時光本身就是一道烏黑的空白。太陽沉下去的時候,護理站會廣播。每個人遛著自己的影子,拿著塑膠小杯去領藥,且要當著護理師的面吞服。一 吞,喉結哆嗦一下,很有一種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意味。那是對生命無謂了。
廣告
一個病友要配一名看護士。看護士最喜歡看報紙。病友看著那些新聞的 表情,就好像那是二十年前,或是二十年後的事。看護士悉心幫病友擦臉,一個個人的表情就這樣被擦掉了。清晨或半夜常有人大哭大叫,我也不外。護理師只會走 到妳面前,拿著一杯水,說:奕含,吃兩顆安定文吧。而妳只能答好。吃藥之後等著藥效把嚎啕壓下去化成淚珠。
院裡有所謂保護室。保護室的天花板、四壁,都是粉綠色泡棉,像個好夢。我想過,除了一直摳泡棉,吞下去,不太可能在那裡自殺。或是他們說的:傷害自己。
如 果病院是我們所有人生命之黑夜匯流的沼澤,那末保護室就是從一個人人生的所有黑夜中舀出最黑的一個夜晚。偶有人被扭打進去,那打鬥很有嬉鬧之意,門打開一 個縫,院裡的燈光扔進去,扔在保護室地上,成為一個金色的平行四邊形,又隨即被拉著對角,扁下去、餒下去、憋成一道鑲在門框上的金邊,人的哀號也漸弱、收 攏,歸於無。
我想,保護室真正的意思是:「保護護理 士」。我們是沒有機會被社會化的人,而保護室是最後的規矩。正如那種描述巴洛克時代畫家的電影,工人扛著金箔大畫框來去,畫框磕在他的肩頸上,他整個人就 像畫中人要掙脫出來。一片金箔脫落了舔在他脖子上,人身最柔軟、柔弱之處。儘管這樣,金還不是他的。
我看著他們,也就是看著自己,好像聖經那句話:「我得知此等婦人,比死還苦,她的心是羅網。」
我也常常想起學測落榜後,準備指考的時光。我總去國立大學 K 館念書。早上五點起床背古文觀止;爸爸載我的路上背單字;七點到 K 館旁的星巴克喝一杯中杯拿鐵配 單字;七點十分進 K 館;唸到十二點去星巴克吃一個可頌,配單字;再一直念到晚上十點 K 館打烊;回家車上再背單字;回家背古文觀止到晚上十二點正;入睡。這 樣怎麼可能不上第一志願呢?因為這個作息一個禮拜只會維持兩天,其餘五天,我都把自己關在房間衣櫥裡哭。
偶爾去念書那兩天,沒有例外,一定 會收到三張以上的紙條。可頌之後,抖擻了濕傘上的梅雨,回座位,有些紙條投進包包,有些貼在筆記上。可以跟妳當個朋友嗎?等一下有空嗎?便利貼掰下來,黏 貼的地方沾上鉛筆跡,筆記上「嘉樹美箭,疏數偃仰,類智者所施設也」,反了,清淡了,在便利貼背面變成「也設施所者智類,仰偃數疏,箭美樹嘉」──意思竟 跟原本一模一樣。
出入 K 館,目光排排螫在臉上,像外頭的雨。收紙條到麻木,只有一個想法:大學生好像很無聊啊。那麼茂盛的慾望,竟也可以滌蕩清澈。小奸小惡叢生、瘋長,最終只有一種喜氣。我再沒坐享過大考那年,眼神一般清潔的季節雨。
唯一印象深刻的一次,是我又第一個地到了 K 館,靠牆背門的座位。有個男生在我隔壁坐下,顯然有意,因為整館是空的。但我也不能問他要幹嘛,顯得自以為是。他轉過身,面對我,把我夾在牆與他之間。他一直搖晃,我的字跡難以端正,盯著數學式子想他到底在幹什麼。
過了幾分鐘才明白,他正對著我自慰。這更不能轉過去,我不想一面讀書一面腦子裡浮現男人的生殖器。很懊惱。他突然站起來,用陰莖碰我的手臂。大考在盛夏,我穿著短袖班服。碰到我的瞬間,我才尖叫一聲。他倒瀟灑,拉上拉鍊,抱著胖書,就走開了。
一禮拜待在家裡有五天。
房間的天下,正文的標楷字與註解的新細明體捉對吻啄,吻啄嘖嘖,嘖嘖如蝗蟲過境,客易主位。黑字是癢癢的天幕,重點星號是星星,整房種滿了短尺長尺紅筆藍 筆,螢光筆的噴泉裡有便利貼泅游,便利貼身上各各有米字胎記。只衣櫥是出世的。妳永遠教不會一件最難穿上的衣服一道最簡單的數學題。衣櫥是我的保護室。從 K 館撤退回家,從家撤退回房間,最終敗退到衣櫥。
抱著自己,衣服下襬的蕾絲如掙扎的眼睫毛來回拂拭我的臉頰,而我自己的眼睫埋在掌心,驚嚇如蟲翅,出水如排泄,恨不能一拳捏死。我要過幾個月才知道,躲在衣櫥裡,視線被百葉切成水平一片一片,正如同精神病院的風景,被鐵欄杆乖巧地切成垂直一片一片。
那幾個月,古文觀止是最大的娛樂。那就是為什麼,當你形容我是「窺之正黑,投以小石,洞然有水聲」──我馬上發現這被扭曲的語境找不到門,一困至今。我為柳 宗元哭過的。你知道嗎?你這個變態了語言的強暴狂。這世界上的一切,正如搭訕的便利貼背後的古文:倒過來念,意思竟跟原本一模一樣。我是生病,但真正生病 的不是我。
每次看見網路上「該去看精神科了」的譏諷,我就很痛苦。甚至準醫生的高中同學亦如此,更痛苦了。這個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想像是多麼扁平啊。在網路上罵髒話的是精神病,在新聞裡砍殺前女友的是精神病──無須診斷,社會自會診斷。
健康的人把「精神病」當作一句髒話;而真正生病的人把樑上的繩子打上美麗的繩結,睡前溫馴地吃兩百顆藥。就像我從未把大學 K 館對著我自慰的男生想成精神病患一樣,那些可以輕易說出「該去看精神科了」的人,真真是無知到殘暴,無心到無情。我幾乎無法羨慕他們的健康了。
——2016.01.07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