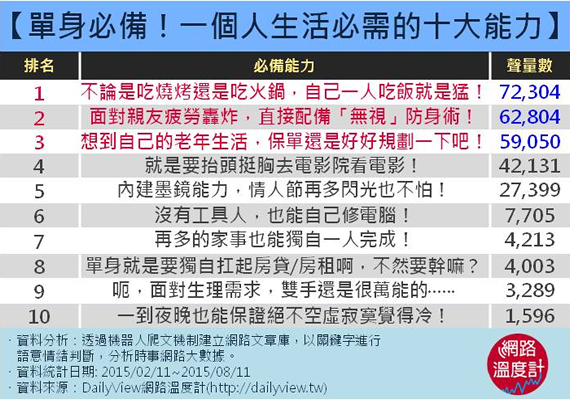我曾在單親家庭長大。沒多久單親家庭變雙親,而且在兩個單親變雙親的家庭長大。
父母親在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離異。自從我懂事,所理解的家庭生活就是有兩個沉默的大人,清早跟晚上出現。進小學才知道家長的作息時間跟他的職業有關。父母都是會計師,父親在政府部門,母親在一個大博彩財團任職,她連星期六、日都去加班。但也不能說他們不愛我。父親常做消夜給我吃,母親每天再晚都會到我房間來查看我的作業。他們單獨跟我在一起時,眼神會透露微笑,但是只要另一個人出現,冷淡就罩在臉上。當然家裡住了一個全職保母做家務、做飯和照顧我。
八歲時有一天下課回家,母親坐在客廳,看見我進門,起身拉著我的手帶我坐下說:「阿囡,媽去香港工作了,你要乖乖地跟著爸爸。」
我望著門旁五個大行李箱,心中感到不祥,叫著問:「你還回來嗎?」
大概母親看見我臉上的驚慌,她摟我入懷中,說「你爸媽離婚了,如果你來香港,可以來找媽媽。」不記得在我懂事以後,母親抱過我,我還暈眩在母親的體味中,她已經起身走向門去。
不到一年父親再婚,娶進惠姨,真的是娶進來。她一來就辭退保母,她享受做家庭主婦,菜越做越好吃。她還喜歡摟著我說話,常榨新鮮果汁給我喝。爸爸回家一分鐘也不閒,倒垃圾,換燈泡,拖地,粗重的工絕對不讓一大一小女人動手。父親正在三樓,在活動梯上,抹樓上的灰塵,他大叫:「惠惠,替我換抹布。」廚房傳來:「正在炒菜,叫阿囡做。」我忙由自己房中出來,去晾衣間大叫:「爸,這有六條,是哪條?」樓上傳來:「最長那條。」我忽然領悟,這才是家庭生活,喧譁熱鬧,無時無刻不交流,我在一個正常家庭度過少女時期。
高三的時候我申請三間香港的大學,當然是為了尋求母愛。母親去香港後,每兩個月都會發一封電郵給我,內容不外乎要好好讀書,做個獨立自主的女人。在我初中一年級那年,她告訴我再婚了。
香港城市大學錄取了我,讀傳播系。我電郵給母親這個消息,她回信說:「我們住在城大附近的義本道,你就住我家,正在準備你的房間。」我大學四年、研究所兩年都跟母親住,所以說我是在兩個單親變雙親的家庭長大。
出了九龍中港碼頭關閘口,母親等在那兒,她的容貌和身材跟十年前一樣好看,可惜我沒有遺傳到一點她的美麗。她身旁站著一個高個子中年人,海藍色的領帶,五官端正,跟母親匹配。他接過我的兩件行李,母親說:「你就喊他蔡伯伯。」
母親的家一塵不染,有工人天天來打掃和做飯。我的房間是淡紫色,牆紙用紫鳶花圖案。母親還記得我喜歡紫鳶花。我進入另外一種家庭,另外一種階層。母親和蔡伯伯說話輕聲細氣地,臉上都帶著微笑。他們在同一家銀行總行上班,他是副總經理,她是會計主任。由蔡伯伯說廣東話的腔調,聽得出他來自台灣。一家三口常去文化中心聽音樂會。
在我二十五歲開始讀博士班的時候,變成了孤兒。在澳門的父親車禍喪生,半年以後,在香港的母親腦溢血過世。他們兩個都只有五十一歲,明明是冤家對頭,為什麼像約好了一起走?是不是在我還沒有出生的歲月,他們有過刻骨銘心的愛情?蔡伯伯辦完母親的喪事就辭職回台灣去照顧他八十多歲的母親。
另外一個變化是我成了富婆。父親的遺囑裡,房子給惠姨,大部分動產給了我。母親義本道的房子和所有動產都給了我,因為蔡伯伯把他那份也給了我,他來自台灣非常富裕的家庭。
在父親周年祭日,我回到澳門跟惠姨一同去氹仔菩提園的靈骨塔拜父親,隨後跟惠姨回老家,她望著我似乎有些猶豫,但還是開了口,「阿囝,我要再婚了……你不要那樣望著我。跟你父親在一起,習慣了被他照顧,習慣了兩個人,這一年非常非常不慣,是你父親的一個朋友。」
我花半年消化了惠姨老伴的觀念。蔡伯伯由台灣飛來跟我一同去上母親的墳。過後我們在半島酒店茶座喝咖啡,我說:「蔡伯伯,現在你身體也好,條件也好,考慮再找個伴吧,我不介意的。」蔡伯伯望了我片刻,只說一句話:「愛不是那樣的。」
本文為鍾玲《單親 雙親》文摘
但同樣是組工會、合法發動罷工,華航與長榮除了勞動條件對比外,企業文化、體制截然不同,機師與空服員的生態與背景也相異,一樣罷工、兩樣情,華航機師與長榮空服員在哪些地方不一樣?《報導者》整理今年前後兩場罷工差異,帶你更認識罷工運動,政府和企業的責任。

長榮空服員罷工8大訴求中,長榮公司強硬表示「禁搭便車」和「勞工董事」絕不退讓,甚至第一時間就以「勞工董事」罷工訴求對工會提告。但相對的,華航卻有勞工董事。勞工董事為何是長榮的紅線?
華航設立勞工董事,源於其官股近半、比照《國營事業管理法》第35條規定,至少五分之一的席次由主管機關聘請工會推派代表擔任董事,勞工董事的權利義務和其他董事相當。不過,過去國營企業工會多由資方輔導成立、普遍關係「融洽」,替勞工權益把關並發揮關鍵的影響力較受質疑。
關於長榮這類民營公司,過去《證券交易法》修法時也曾提出增設勞工董事相關規定,但修法未果。目前,民營公司僅有「獨立董事」,沒有勞工董事的法源依據。
長榮董事會僅有6席一般董事、3席獨立董事,若釋出或增設一席董事給工會,即可能對董事會決策有影響力,這是長榮資方不惜提告反制工會、堅決不開放勞工董事席次的主因。

雖然目前台灣沒有法律要求民營上巿公司需設勞工董事,但只要該公司董事會同意,也可以設立勞工董事。
以德國為例,在二戰後,大企業開始設立勞工董事,最早也是勞資雙方協商出來後,才慢慢藉由立法去完善勞工董事的制度,像是BMW等大公司都有勞工董事。1998年,德國勞工董事制度確立50週年時,有很多研究指出,大部分資方團體都認為勞工董事參與管理是好事,對於增強員工向心力是有幫助的。
不過,德國企業的董事依職權區分「管理董事」、「監督董事」等,在職權分工上規範得相當明確和精細。台灣未來若要讓民營企業的勞工董事明文入法,權利義務也應討論。

華航機師罷工時,交通部一開始站在第一線斡旋,勞資5度協商達成共識後,才由勞動部次長劉士豪出面宣布結果。而長榮空服員從罷工投票開始時,行政院即指示成立專案小組,交通部處理疏運、勞資爭議則由勞動部處理,為何有這樣的差異?
主要在於華航仍是官股近半的「半國營企業」,交通部能以「大股東」身分插手;但長榮是百分之百民營公司,過往飛安紀錄算是國內航空業的優等生,交通部民航局現有的政策工具,例如航權分配,都是看飛安與服務,沒有一項評分是與勞資爭議有關,交通部沒有政策工具可以逼資方上談判桌,因此長榮空服員罷工,從一開始就由勞動部站上前線負責協調。
事實上,勞資糾紛處理單位本來權責就在勞動部,因為相關的勞資權利義務法規,勞動部也比較清楚;只是勞動部沒有政策工具逼迫資方,協調罷工時間勢必會拖得比較長。

華航機師罷工,最後7天落幕,已被喻為馬拉松戰。但此次長榮空服員罷工,長榮公司第一波就一口氣調整了一個星期的航班因應,空服員工會也以「慢跑到最後」做為內部社團名稱,為什麼空服員比機師罷工更可能打持久戰?
空服員從受訓開始都是一整個班,同期姊妹間的感情好,以長榮777機型為例,一班機空服員約在10到15人,在機艙內相互支援、工作狀況能互相理解,因此長榮空服員工會成立時,3天內就有1,500人入會員。但機師則是學長學弟制、工作場域上交會時間也不多,習慣單打獨鬥,團結度上不如空服員。
此外,依照民航局規定,每一個飛機艙門至少要配置一位空服員,確保緊急事故時可協助旅客疏散,不同機型、空服員都要通過適航驗證,並非什麼機型都能上機執勤。
因空服員團結性強、每個班機人力需求又大,一旦空服員罷工,資方人力調度遭遇的難度甚至比機師罷工更高 ,所以長榮面對空服員罷工,一開始就先調整一週的航班調度,7天預計取消625班,比起華航機師罷工7天取消214班,影響更大。

華航和長榮都是上市公司,股東依法選出董事,董事再選出董事長;不過,半國營的華航,過去董事長多是「政治任命」,今年初機師罷工後,府院高層主導下,撤換罷工事件處理不佳的原董事長何煖軒。民營的長榮航空,雖然沒有政治包袱,但若因罷工危機處理造成公司營運和品牌損耗,也需對眾多投資者交代。
兩大航空公司雖都背負公共運輸的責任,也同樣面對董事和股東,但華航有官股在身,擔負更多的公共責任,最大股東交通部需要對納稅人負責,在董事長選任的政治責任上也無法逃避;而百分百民營的長榮,雖不像華航有那麼多政治包袱,但公司經營仍須對董事會和所有投資的股東們負責。
倘若投資人認為長榮的罷工危機處理不佳、影響公司整體營運,讓投資人和股東獲利受損,也可透過董事會去表達意見、甚至改選董事長,選出適合經營公司之適當人選。

長榮空服員罷工後, 長榮揚言若因而虧損可能乾脆縮減航線、縮小規模。 不過,如果只是因為罷工短暫影響就要縮小規模、減少人力,可能違法。根據《勞動基準法》第11條第2款,雇主非於有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不得任意解僱勞工,罷工不在上述範圍內,更何況長榮航空是上市公司,因虧損要縮小規模,恐怕會讓市值大幅縮水,這不是資方會樂見的結果。
即便真是因為公司虧損、縮小規模,若涉及大量解僱的話,也必須要依照《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》的規範。但不管長榮罷工最後如何收場,勞資雙方是否有簽訂團體協約,只要罷工是合法的狀態下,事後資方對於參與罷工的工會成員進行的任何懲處甚至資遣,都極有可能違反《工會法》等相關法律,被勞動部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認定為是「不當勞動行為」而開罰並撤銷。

長榮空服員罷工,進入第6天,勞資雙方僵持不下,罷工協商談判仍未啟動,罷工影響持續擴大,要讓罷工傷害縮減,政府應該重新劃分權責,交通部出手敦促資方、勞動部勸說勞方,讓雙方在訴求上各退一步,儘早坐上談判桌。
即使長榮是百分之百民營公司,經營的航空事業仍是特許行業,交通部可以政策工具敦促資方盡快提出方案協商,並應停止協助長榮因罷工影響的離島航班疏運,避免讓資方有恃無恐的持續對抗罷工。
另一方面,勞動部則應積極調解,尋求勞資雙方都可以信任的第三方公正人士,擔任協商主持人,第三方公正的仲裁人通常具備勞資調解經驗,較能從勞資雙方提出的方案中尋找最大公約數,並緩和勞資雙方針鋒相對的氣氛。罷工協商往往最後不是讓勞資任何一方全拿,而是尋求一份勞資雙方都能接受的「折衷方案」,才能讓罷工儘早落幕。
諮詢專家/邱駿彥(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教授)、周聖凱(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副祕書長)、林佳和(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)、廖郁晴(文匯法律事務所律師)、吳俊達(執業律師)




 郭台銘眼見有記者鞋帶鬆了,突然戲劇性地蹲下幫記者繫鞋帶。(攝影:張家銘)
郭台銘眼見有記者鞋帶鬆了,突然戲劇性地蹲下幫記者繫鞋帶。(攝影:張家銘)